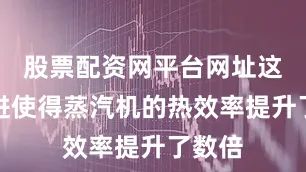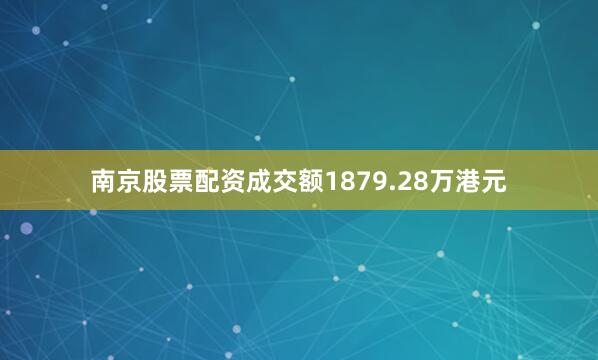在每个人的生命中,总会存在一些令人难忘的回忆。对于王成刚来说,那段在陕北插队落户的岁月,终将成为他心中不灭的印记,无法释怀。尤其是提到那位孤独的韩大伯,他的心中总泛起一阵难以言喻的酸楚与痛苦,因为当年他曾保证会常来探望韩大伯,然而却因时光流逝,未能及时履行这一承诺。
王成刚于1969年1月下旬从繁华的北京来到陕北,他们所插队落户的村庄名叫韩家沟大队,这个地方呈现出典型的“两山夹一沟”的地形,坐落在一条贫瘠的小山沟中。这条小山沟里仅有两个生产小队,分别是韩家沟一队和二队。来自北京的十三名知青被分散到这两个小队中,王成刚和其他六名青年被安排在了一队。他们暂时借住在当地居民的家中,与乡亲们一起搭伙吃饭,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
其中,一名叫杨庆贤的男知青与王成刚共同借住在孤独的韩大伯家。他们三人同住在一处简陋的土窑里,挤在一张狭小的土炕上,生活的艰辛与乡土的气息交融在一起。第一顿晚饭是在队长韩玉田家享用的,算是为他们接风洗尘。七名来自北京的知青围坐在一块旧门板上,菜品虽极为简单:半盆土豆炖酸菜、半碗咸菜以及半碗辣椒酱,每人盛一碗玉米面糊,简陋的玉米蒸馍则是随意享用。虽然饭菜简单,却意外地让每个人都吃得心满意足。
展开剩余82%饭后,王成刚和杨庆贤返回韩大伯家。韩大伯的居所有两孔土窑,其中一孔是冷窑,用来储存农具和杂物,而王成刚与杨庆贤所住的这孔則显得宽敞一些,炕的上面铺有一张破旧炕席,炕的内部则是一个灶台,灶台上安放着一口七印铁锅,供三四个人用餐毫无问题。窑内光线昏暗,靠后则有两个大罐,韩大伯告诉他们那是他存粮的地方。在这简单的土窑中,尽管东西不多,却打理得干净整洁,处处流露出一种温馨的家庭氛围,虽说家徒四壁,但却弥漫着家的温暖。
那个晚上,韩大伯特意将自己的铺盖移到了炕边,把炕头留给王成刚。杨庆贤的铺盖紧贴在王成刚旁边,而韩大伯与他们之间保持着一段距离。他开玩笑地说:“北京的娃娃讲究卫生,我一个光棍汉,怕你们觉得我脏。”虽然看似俏皮,却流露出他内心对这两个年轻人的在意。
韩大伯不仅是个独身汉,更是个能干的农村人,人人都称赞他。他把院子打理得一尘不染,更是将茅房旁边堆放的柴火整理得整整齐齐,像一座小型的木材仓库。每天早晨,韩大伯都会洗好手,才叫王成刚和杨庆贤起床吃饭,他体贴地说:“你们俩坐了好多天的车,路上辛苦,想让你们多休息一会。”
随着日子的推移,韩大伯像家长一样细心关照着王成刚和杨庆贤。他们去水井挑水时,韩大伯总是跟随在侧,反复确认他们会打水后,才敢放心。这让两人感受到一种家的温暖,仿佛时间的流逝让他们之间的情感加深。
在安顿妥当后,天气晴好的时候,韩大伯就会带着队里的羊群去沟坡放羊。冬天没有新鲜草,沟坡上的枯草也不多,因此在恶劣天气时,他便不出山放羊。而队里储有谷草、豆秸和玉米秸杆,虽然不出门,但也能保证羊只的温饱,每天傍晚给羊群饮水就足够。
春节临近,韩大伯为了给王成刚和杨庆贤准备一顿像样的年夜饭,秘而不宣地将家里那只大公鸡杀了,炖了两大碗鸡肉。而吃饭时,韩大伯却没有动过一口鸡肉,他只是淡淡地说:“我不爱吃鸡肉。”这背后,王成刚事后回想,发现韩大伯的眼中似乎闪过泪光,那是对这只公鸡的依依不舍。
春耕开始后,王成刚和杨庆贤每天都参与劳动,韩大伯每次早晨都会为他们准备好饭菜,然后才出门放羊。傍晚,王成刚和杨庆贤回到家时,韩大伯总会在灶台前等候着,笑着说:“你们累了一天,快去休息吧,我来刷锅洗碗。”对于这样的关心,王成刚心里暖暖的,有时他也会抢着刷碗,韩大伯却不乐意,总是把他驱赶去歇息。
某天下雨,他们在田间种红薯,衣服都湿透了,胶鞋沾满了泥土。晚饭后,韩大伯将洗净的碗刷好后,又帮助王成刚和杨庆贤烤干了湿衣服,还替王成刚缝补了袖子上的一个破口。这样的照顾让王成刚和杨庆贤倍感温暖,他们在韩大伯身上领悟到了如父般的关爱,心中流淌着感激。
那年初秋,农队为知识青年修建了三孔新窑洞,成立了知青点,七名北京知青纷纷迁入新居。当搬家的那天,韩大伯泪如雨下,哽咽着说道:“你们走了,窑里又剩下我一个人,心里实在不舍……”他的话让王成刚深感不忍,也让他更加珍惜与韩大伯的情谊。
王成刚和杨庆贤搬离后,韩大伯每次见到稀罕的东西,总是忍不住送给他们。即便是从山上摘来的酸枣或野果,他也觉得不舍得自己吃。那棵院子里的老枣树每年结的枣,几乎都让王成刚和杨庆贤享用。
1970年冬,王成刚经过集体的征兵体检,其中只有两个人成为兵员,他便是其中之一。得知王成刚即将入伍,韩大伯双眼含泪,心中五味杂陈。他为王成刚感到高兴,虽为其离去感到不舍。入伍前一天,韩大伯特意跑了五里路,割了二斤羊肉,还推磨了四斤麦子,亲手为王成刚包了羊肉饺子,并特地买了一瓶烧酒和两斤豆腐请韩队长和杨庆贤一同来庆祝。为了给王成刚送行,韩大伯甚至提前将过年的麦子用尽,为的就是这顿饺子。
当王成刚离开韩家沟的那一天,他将自己的行李及生活用品留给了韩大伯,而韩大伯却坚持要塞给他十块钱,王成刚虽然心生感动,却又不好拒绝,最终还是收下了这份厚重的情谊,并委托韩队长将钱物归还。
那天,韩大伯含泪将王成刚送到村口,哽咽着说:“到部队上要好好干,一定要有出息。”王成刚含泪回应:“大伯,您放心,以后我一定会回来看您的。”这一别,可谓是人间的长久分离。
王成刚在军队中的表现优异,凭借自己的学历与勇气,一年后便被安排到军校学习,毕业后担任连队的司务长,后来更是升任连指导员。时光如梭,1977年年底他准备回北京探亲时,突然想到了陕北的韩大伯。由于工作繁忙,他在部队时只给韩队长写了两封信,每次都通过韩队长向韩大伯问好。想到韩大伯对自己的照顾,心中不觉愧疚,于是决定将自己准备带回北京的军大衣、军用水壶和一张四寸照片寄给韩大伯,还给韩队长和韩大伯各寄去了二十元钱,以表心意。
回到部队后不久,王成刚收到了韩队长的回信,信中说韩大伯身体很好,穿上了寄去的军大衣在村里走动,引得乡亲们纷纷称赞,而韩大伯满脸骄傲地对人说:“这是我北京娃娃寄给我的!”韩队长还告诉王成刚,韩大伯背着水壶,再也不会口渴了。
1986年秋,王成刚转业回北京,心中原计划一切安顿好后再去陕北看望乡亲与韩大伯。然而,由于工作十分繁忙,他的计划却一再耽搁。直至2012年,王成刚终于在退休后找到时间,与杨庆贤重返陕北。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雨之后,陕北的面貌已然焕然一新,许多乡亲都不再识得两人,当年的韩队长也近八旬,而韩大伯则已去世两年多。
王成刚来到了曾经的韩大伯住处,看到土窑塌陷,院子里满是杂草,他和杨庆贤心中的哀痛无法遏制,泪水夺眶而出。随后,韩队长带他们走访了当年的知青点,那三孔土窑历经风雨,仍保持完好。中间那孔窑的墙壁上,挂着一块木制牌匾:韩家沟一队知青点。
打开窑门,内部一尘不染。墙上挂着一个镜框,里面正是当年王成刚寄给韩大伯的那张穿军装的照片,旁边还悬挂着水壶,正是他曾寄给韩大伯的。这一切,逐渐拼凑出了一段充满温情的回忆。
原来,韩大伯的那两孔土窑在被评定为危窑后,队里便安排他居住在了知青点,省去了生活的后顾之忧。韩大伯在去世前将积蓄全部捐给了队里,留下的十几只羊也分给了乡党们。他曾对韩队长说:“窑里的东西不要动,等王成刚回来看到这些,便仿佛看到了我……”听闻此言,王成刚心如刀绞,眼泪再次夺眶而出。
那次回陕北,王成刚和杨庆贤前往韩大伯的坟地祭拜,给韩队长留下了一些钱,同时慰问村里的老人们,带着一份深深的愧疚回到了北京。多年后,每当王成刚想起陕北的韩大伯,他的心中便会涌起难以名状的情感,尤其是回忆起韩大伯为他准备饺子的场景,内心的痛楚让他无以自已。诚实善良的韩大伯,成了他心中永存的牵挂,韩大伯将永远活在他的记忆深处。
——作者:草根作家
发布于:天津市融正配资-中国前十大证券公司排名-查配资App-配资门户网网站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